万里长征走完了,但革命的路还长着哩。中央红军到达陕北,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红军计划的破产,预示着革命新高潮的到来。党中央正在部署新的战斗任务,让会师后的各路红军,打一场“开门红”的歼灭战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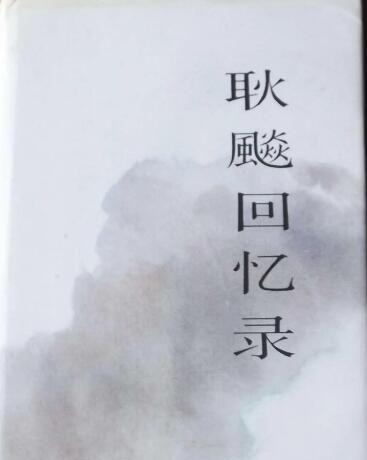
毛泽东同志亲自组织我们去看地形。我们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十五军团的团以上指挥员先在张村释会合,然后骑马到一座山上去观察战场。山脚下有一个百十户人家的小镇,我们展开地图,知道这个三面环山、一面临水的小镇就是直罗镇。
根据毛主席的部署,左权同志带着我们这些参谋长们转了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,大家现地标图,明确了战斗任务,各路指挥员举着望远镜,都不约而同地对直罗镇东边的一个小寨子多看了几眼。这个小寨子,有点像江西苏区的“土围子”,有可能被敌人利用。于是决定:战前派部队拆毁它。
部队里那些老兵,一看我们的行动,知道有大仗打了,真是磨拳擦掌,枕戈待旦。待机地域的各部驻地,不时飞出一阵阵《会师歌》:
南北红军大会合,
同心协力来救国。
一个英勇善战不怕困难多,
一个万里长征打遍全中国..…
当时,蒋介石不顾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向关内推进,蚕食华北;而是孤注一掷,投入大量兵力向红军“围剿”。中央红军一到陕北,敌六十七军、五十七军便向富(娜)县一带合围,意欲在葫芦河与洛河之间与我军决战。
当时正值十一月中旬,陕北已近寒冬,河流结冰,天空飘起清雪。从江西苏区一直为我作警卫员的杨力同志,这时已是副连长了,却一直还穿着一身夹衣。尽管当地人民作出了大力支援,部队中仍有部分同志还没换上冬装,个别的甚至还穿着短褂。我设法给杨力搞了两块毡,小得可怜,只能一前一后,当作背心。杨力见我有些过意不去,便说:
“参谋长,你莫费心了。等打完五十七军,我们肯定能换装了。”

五十七军属东北军。士兵都装备有棉衣棉鞋、狗皮帽子,军官还有皮大衣。杨力的话,使我感到了红军官兵敢打必胜的决心。
敌先头部队五十七军(董英斌部)一O九师,果然如期进入直罗镇。他们在六架飞机掩护下,沿结了冰的洛河开进我军为他掘好的坟墓。这个师的师长姓牛,所以部队中响起一片“捉牛”的呼声。
十一月十三日,我军展开总攻。一军团由北向南,十五军团由南向北,把敌人包围在直罗镇三面环山、一边临水的山谷里。
战斗在拂晓打响。左权参谋长在电话里询问战况。我告诉他敌人毫无准备,已经被打乱了营。他又问东北军与南方军阀的部队有什么不同的特点。由于我正在组织战斗,还没来得及归纳总结,便告诉他:
“特点就是—这些敌人在投降时,知道先用白毛巾向我们摆几下。南方的敌人很少有这样做的,跪地投降而已。”
左权参谋长笑起来:“好嘛,这说明东北军比南方敌军规范些,知道使用国际通用的信号。”
敌人的地面指挥体系被打乱,但天空飞来六架飞机助战,进行垂死挣扎。敌师长牛元峰躲进镇东北那座破寨子里,死守待援。我们于当天中午解决了谷地上的敌人。晚上又去攻那座土寨子。这座土寨事先已被我十五军团拆毁,残敌仓惶加以修复,在里面呼叫附近的敌一O六师前来营救。
这时已不可能有援兵来。牛元峰只好向黑水寺方向逃跑,但终于还是被活捉了。
直罗镇全歼一O九师,师长牛元峰以下官兵五千三百多名被俘,缴获各种枪枝、小炮、电台四千余件,子弹二十二万多发。大批被服落到我们手中。毛泽东同志在一方面军干部大会上对这次战斗作了很高的评价。他说:“长征一完结,新的局面就开始。直罗镇一仗,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,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,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,行了一个奠基礼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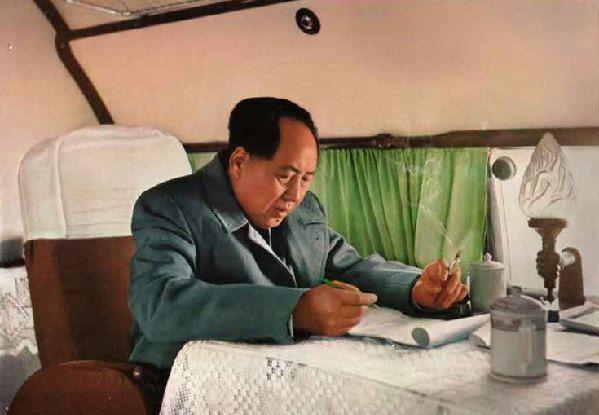
敌一0九师覆没于直罗镇后,红一军团又冒雪奔袭太白镇,将敌一0六师一个团歼灭,其残余兵力仓惶逃遁。一0六师是敌人第二梯队,他们一逃跑,其他各部一发不可收拾,纷纷向合水一线退却。同时,敌东路军也放弃鄜县(今富县)。蒋介石发动的对陕北第三次“围剿”宣告破产。
但是,敌一一0师仍然占据甘泉。甘泉是延安南大门,为延(安)西(安)公路上的咽喉要塞,地理位置十分重要。直罗镇战役后,毛泽东、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回到瓦窑堡,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,将彭德怀同志留在前方,指挥各部箝制敌人。接着,我们奉命围攻甘泉。
我与杨得志同志组织部队向甘泉进发,部队由于新胜,士气很高,行军十分活跃。当时我与杨得志同志都换了新的坐骑,他是一匹白马,我是一匹青马,那马膘肥体壮,真像唐三彩的瓷马一样,背阔鬃长,臀部浑圆。陈赓同志便鼓动我们赛马。那时我们正当二十多岁,对这类活动很有兴趣,于是拍马奔驰,杨得志同志渐渐冲到了前头,引得部队阵阵喝彩。哪知正在兴头上,马前的草丛里突然窜出一只野兔,白马受惊,急停躲避,将杨得志同志抛下马来,他当时竟昏了过去。
我急出了一身汗,赶紧给他做人工呼吸,警卫人员赶上来,将他抬到马上,走出二十多里路,他才缓过劲来。以后杨得志同志再也不骑那匹马了。前年我们两人还谈起当年那次“赛马历险记”,为年轻时的鲁莽而慨叹。
甘泉县城是一个傍山大镇,城墙虽是用黄土夯成的,但十分结实,有一半在山上,有一半在河边,确实易守难攻。我们周密侦察后,决定从靠山的那面爆破,炸开缺口冲进去。
担任爆破的仍然是长征路上担任架桥的王耀南同志。
王耀南同志报给我一个爆破方案,计划用挖地道的办法,向城墙底部打一条隧道,到达城墙后,开出药室,然后装上炸药引爆。这个办法在没有石头的黄土高原上,无疑是个减少伤亡、隐蔽接敌的好方案,但计算隧道长度,在当时却是一大难题,工兵营找了一些小“诸葛亮”,反复核实,最后报给我一张图纸,我问是否准确,他们说,不但计算无误,还利用夜暗实地丈量了长度,万无一失。
于是工兵开始作业,我便亲率突击队准备攻城。几天后,隧道挖成,借了老乡一口棺材,装满炸药放在隧道尽头的药室里,突击队同时运动至出击地域,只等一声巨响,突袭入城。
那天是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月黑风高之夜。我伏在突击队的前沿,等各路人马报告就位后,用电话向王耀南下令:
“起爆!”
一千斤TNT炸药的威力,真有山崩地裂之势,爆烟窜起几十米,把守敌的城墙严严实实地捂了起来。不等土块、断枝落完,我们率突击队向炸点扑去,哪知到达预定的突破口时,我们才大吃一惊—城墙根本未被炸开,倒是在离城墙几米远的山坡上,掀开一个大洞。原来,问题出在我最担心的计算上:山坡是斜的.,隧道是直的,按数学上的三角原理,正是一个标准的“勾、股、弦”,而搞计算的同志仅仅按水平距离算出了隧道长度,没有把三角关系考虑在内,因此,炸点与城墙误差甚远。
爆破失败,但我们突击队已兵临城下,因此,我们下令在城墙上挖洞,重新组织直接爆破。守敌开始被巨大的爆炸声吓蒙了,这下已缓过劲来,紧急组织增援。一我们所处的位置是城上守敌的射击死角,于是他们便丢手榴弹。由子距离太近,从城墙上扔下的手榴弹直接落在我们身上,我们便抓住弹体“回敬”回去。尽管如此,还是有几枚在附近炸开了,我只觉耳边“嗡”一声,一块弹片在耳朵下边的脖子上划了一道大口子;鲜血滋出老高。
这样,临时爆破无法实施,加上我已负伤、突击队的营长便组织掩护撤退,后续部队见我们没有得手,亦停止了攻击。
脖子上的伤口不能象四肢上的伤口那样捆扎止血,幸亏我有随身携带的云南白药,还是在长征路上一位好心的老馆子送的,便敷上一些,果然十分灵验。
陈赓、罗瑞卿、杨得志等同志纷纷来看我的伤势,他们都十分着急。陈赓同志说:“哎呀,我们离军团部这么远,姜齐贤同志又没.随一纵行动,这可怎么办哪?’’我说:“不必大惊小怪,离掉脑袋还远着哪,我还可以骑马呢!”
正说着,彭德怀同志闻讯赶来,一看伤的位置,大叫“不好,只用点白药凑合可不行。”他立即叫警卫参谋要通十五军团徐海东同志的电话,请徐海东同志让戴部长火速赶来。
当时,徐海东同志病得很厉害,中央领导同志把红军最好的医生,即卫生部长“戴胡子34派给他了。徐海东同志一听我负了伤,立即把自己的骡子给戴胡子骑,让他星夜奔驰二百多里,赶到甘泉前线。
戴胡子一见面就责备我:
“耿飚你不要命了?伤到这程度还骑马到处跑l’’
我说:“戴胡子你别大惊小怪。我的伤我知道,不过削了块肉去,没伤着骨头。”
他说:“伤了骨头你早完了。你知道这是什么部位?这是‘危险三角区’二,紧挨着大动脉,周围全是淋巴腺,你住院吧。
打下一O九师.,卫生部也缴获颇丰。戴部长大大方方地用生理盐水为我清创,还打了消炎针,绷带也是崭新的,再不是江西苏区时那副“小家子”气了。
我说:“你老兄怎么阔绰起来了?”
他外吃一笑:“我的参谋长,不瞒你说,给你用的全是兽医药品,一O九师的兽医营被我们抄了。”
我半开玩笑地说:“你可别把我治死了。”
他说:“放心。起码比在江西时用茶叶水洗伤口保险得多。”
红军医院住在甘泉附近。戴胡子每天清早都到结了冰的洛河边去冲澡。当时寒风凛冽,一般人穿棉衣都觉得冷,而他却脱得赤条条的,把冰水一盆盆地往身上浇。这种冬浴是他长期养成的习惯。冲完澡他的身上皮肤潮红,热气腾腾。我也想学习这种锻炼身体的办法。戴部长说:“那可不行,得从小坚持。你想健身可以练练武术嘛。”
戴部长让我注意伤口,不要多动,以免扯破动脉或者引起感染。但是我闲不住,还是经常到甘泉前线去看看。
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,毛泽东同志在瓦窑堡做了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》的重要报告,明确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政方针,因此,对甘泉基本上实行围而不打。这时,中央把贺晋年同志的八十一师加强给我们。
守城的东北军在铁桶似的合围中断了粮草,只能靠空中接济。每逢敌运输机临空,战士们便用步、机枪射击,使它不能按理想的航线飞行,只得把食品胡乱扔下来,其中一半以上落在城外,我们就一拥而上,用早已备好的三角钩抓住食品包,连同还没落地的降落伞一块拖回来。由于降落伞仍有张力,几百斤的空投物资不用费多大力气就可轻巧地取回。敌人空投的食品大部分是烙饼,每个十几斤,一袋十个,每个降落伞上吊着二至三袋。
当时彭德怀同志很忙,既要指挥作战,又要通过渠道与东北军、西北军接触,做统一战线工作。在我养伤期间的一天中午,他风尘仆仆地来到我们驻地,进门就喊:“耿飚,快搞饭来吃1饿死W;我说:“你这个老总哟,总是突然袭击,现在上哪给你搞饭嘛。”彭德怀同志说,什么都行,能填肚子就行咯。我到伙房一看,只有一块腊肉,正巧我养伤时,用小木棍串了一串大蒜养在水碗里,放在窗台上让它生芽,原意是增添一些房内生气,现在已有五寸长了,倒也郁郁葱葱,生机盎然,便统统剪了下来,给彭总炒了一盘腊肉蒜苗。彭总一见,连呼好的好的,抓起缴获的烙饼,大口吃起来,看那样子,他确实饿坏了。

彭德怀同志当时正与东北讲武堂的高福源谈判,让他去做张学良的工作,联合抗日、一致对外。后来这个高福源果然起了很好的作用,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“西安事变”后,这位抗日志士被蒋介石杀害了。
彭老总为了让我安心养伤,把他的一个警卫员派到我处,连同我原来的警卫员和公务员,共三人“看”着我,并嘱咐他们:“看好你们的参谋长,别让他乱跑。”我没有办法,只好老老实实养伤,乘此机会,我让通信员把我的文件包拿来,以便整理一下文件和笔记、杂物。
长征中我有一架照相机,拍了不少照片。有战场风光的,也有俘虏群或战利品的。大多数是为同志们拍的生活照‘我还坚持了天天记日‘记。翻着那本厚厚的_日记,一路上的山山水水又浮现在眼前。
日记上记载着我们先后攻占的几十个城镇,跨过的十多个省区,建立的数百个苏维埃政府,上千名支援过红军的各族人民。一年中,打仗的时间仅有月余,休整的时间六七十天,其余的二百六十多天,我们一直是行军,这真是一次名副其实的二万五千里远征啊!
长征使我这个不会游水的“旱鸭子”,不得不在枪林弹雨中渡过一条条湍急的河流。有于都河、信丰河、潇水河、湘江、清水江、乌江、赤水河、北盘江、金沙江、大渡河、白龙江、渭河、洛河·一以及它们数不清的支流。为了夺取那些险要的关隘,我姐还翻过了五岭山、苗山、雷公山、娄山、云雾山、大凉山、六盘山……这些山中大大小小的山峰上,都留下了红军的一串串足迹…
使我久久注视的还有那些在长征中拍下的照片,许多战友已经长眠了。
这是毛振华烈士,强渡乌江的英雄。他在桐梓城留下的身影,充满了青春活力。他老是念念不忘,在“八一”起义后,丢失了一把为贺龙同志保管的小勺,总是担心“胜利后见到贺军长该怎么说呢?”……他没有等到那一天,在长征最后的一场战斗里,洒尽了青春热血;
这是黄甦同志。他是省港罢工的纠察队长,广州起义的敢死队长。在藤田改编时,我们曾吃过一次只有盐巴的“白斩鸡”。在草地绝粮的时候,我们猎到了一只黄羊,可他又偏偏是个不吃羊肉的人,当时我只能拿出最后几支烟让他压压饿。他看我抱歉的样子,开朗地说:“参谋长你不用遗憾,等到了根据地,你尽管请我吃鸡、吃鱼、吃肉,我会有请必到的。”我说:“黄政委,讲定了,到时可别不来哟}”哈达铺改编时我们分手,他到四团去代理政委。直罗镇战斗之前,他接到了到新单位去任政委的通知。由于杨成武同志(改编后任团长)住院,他坚决要求打完再走,谁知竟不幸中弹,把鲜血浇在了奠基礼的土地上;
永远留在直罗镇的还有原红四团参谋长李英华。他可真是名符其实的一代“英才”和“精华!a.在我们所有的合影里,他总是用右手卡着腰,似乎随时都要投入战斗。就在他已经担负起指挥一个团的重任时,被敌机打中,我军又一颗将星溢然损落……;
这个总是以马为背景的是我的马夫老谢。福建建宁人,长着北方人般的络腮胡子,憨厚得象个庄稼汉。在两河口,我那匹骡子走失后,他难过得三天没吃下饭,只是一再吧着旱烟袋生自己的闷气,想一阵,捶着自己的脑袋骂一句:“该死哟!’’在水草地上,他把能找到的食用草都喂了马,自己吃棉絮……他在走出草地后的白龙江栈道上,为了哄马过山,失足掉进了深渊……;
哦!这个只留下一张照片的是我的叔叔—我从家乡带出来当红军的耿道丰同志。他是四团通信排副排长。长年累月的蔑匠生涯使他的背有些询楼,人们爱喊他“s醴陵驼矛”。他打的草鞋是全团闻名的,总是比别人打的多两道绊子,又结实又跟脚,有多少同志从他那里领到过草鞋哟……
他病倒在乌蒙山那雾蒙蒙的深林里,与大山化为一体了。战友们只能把一个电话线的木拐埋在他的坟头,算是墓碑吧!
一九三六年,我在“红大”学习,莫文骅同志曾对我说,让我们写一本长征二万五千里的书吧!我说,应该写,我有日记和照片为素材。他对这些宝贵的资料赞叹不已。由于斯诺正在延安访问,陆定一同志把这些照片和资料借去供他参考,可惜辗转丢失了。只有那架老式照像机,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它曾见到的一切。
我补记了直罗镇战斗的日记。.明天,将有新的征途在等待着我们。